司法判決可接受性論文
一、概念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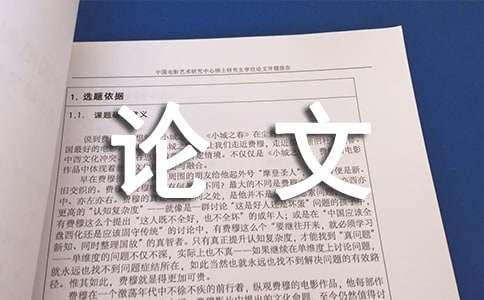
(一)司法判決可接受性的含義
司法裁判是法院對當事人具體爭議的判斷和處理,其標志著法庭審判活動的終結。司法判決可接受性是指依法作出的司法判決在社會民眾之中的認可程度。當然這里的社會民眾既包括法律人又包括普通民眾。法官通過司法判決的方式表達對當事人雙方爭議的理性判斷,并且法官作出的每一判斷都是有法律作為依據的。但是,一個完全依照法律作出的裁判在現實中卻并不一定得到普通民眾的接受。諸如幾年前的“藥家鑫案”,從法律人角度看,藥家鑫的卻有從輕情節,殺人手段也并不殘忍,筆者當時也認為最多會判到死緩。可是當事情在網上鬧的沸沸揚揚,網民情緒異常憤怒的情況下,“民意”將藥家鑫送上了死亡之路。試想,在風口浪尖上的“藥家鑫案”如果沒有按所謂的“民意”處理,會不會產生諸如上訪,鬧事等惡劣的社會后果。總之,司法判決可接受性需要兼顧法律和社會兩個層面。
(二)研究司法判決可接受性的意義
現代公權力的運作,不管司法、立法還是行政中,都應考慮可接受性,公權力運作中應充分建立在商談理性的基礎之上,司法審判也應朝這個方向發展,這適應了國際法律發展的潮流。從現實來看,很多當事人對司法判決的不滿意并非處在合法性、公正性的問題,當事人多次上訪或申訴,這也要求不得不研究判決的可接受性問題。從理論上看,雖然合法性、公正性是司法重要的價值目標,但不是司法惟一的目標。良善司法應當具有多面向性。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司法要回應這種要求,必須研究司法審判的可接受性問題。合法性、公正性不能涵蓋司法的所有價值,合法的前提是嚴格依法辦事,更多的適應了法律形式正義的要求。法律本身是不完善的,立法的優點和缺點是聯系在一起的,缺點是優點的延長。如果僅僅以合法性為標準很難使一個案件做到盡善盡美。公正性不能涵蓋可接受性,公正本身也具有不確定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公正只是公眾最大的公約數而已。
二、修辭在我國古代司法判決中的發展及其對判決可接受性的影響
在我國,司法判決中修辭手法的使用可以追訴到古代。從漢代的司法實踐上來看,司法者在進行判斷時,不僅依據法律對當事人的行為進行判斷,更是引入儒家經典來進行斷案,甚至經義與法律沖突的時候優先適用儒家經義。同樣的案件,根據當事人的主觀心態不一樣會產生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這種引經入律的形式也對后世的司法裁判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在疑難案件的處理上。根據筆者的推斷,這種風格影響者司法判決的說理手法,增加其可接受性。真正有史料記載的在司法判決中出現修辭的是在唐代時期,只是最初在司法判決中出現的種種說理性修辭是出于對上級匯報的目的。南宋之后的古代中國的司法實踐中,修辭的受眾開始面向普通民眾。特別是在婚姻家庭和鄰里糾紛案件中,司法者在作出裁判時更加考慮普通民眾對裁判的接受和服從程度。南宋時期是我國司法判決說理性修辭技巧發展的巔峰時期,在延續唐判的重分析、說理的技巧外,南宋判決在注重對案件基本情節和事實的描述前提下,注重對現有證據的分析和運用輔以推理論證以及強化對不同情節的說明,來增加其判決的可接受性。其次,南宋判決在法條援引上避免了生搬硬套的引用方式,將法條的援引與司法判決說理相結合,達到情理法三者結合。再者,南宋的司法判決注重寓教化于判決。其不僅使司法判決在文本表述上顯得更合理,使民眾更易接受,同時也在司法判決履行過程中教化民眾。所謂“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民眾在理解和接受判決不僅僅是懼怕法律的強制力,而是認可法律,知曉自己的行為的不當之處,自愿服從法律的處罰。
三、影響司法判決可接受性的修辭技巧
修辭是關于“話語者”、“受眾”和“話語方式”的問題。修辭方法已然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法律方法,在法律領域,“話語者”是固定的———國家審判機關,所以在選擇修辭方法的適用時主要考慮兩個方面,首先是話語的“受眾”,也就是言辭的接收者;而后是言辭所處的“語境”,也即言辭在什么情形下表達。
(一)根據受眾的差異選擇不同的表達形式
亞里士多德是古典修辭學的創立者,其修辭學說很注重根據聽眾的年齡、財富等不同情況的劃分,對其采取不同的對話形式。這里我們所說的聽眾就相當于司法判決書中的受眾。對于司法判決書來說,要提高司法判決書的可接受性必須從把握司法判決書的受眾上做起。首先從案件的雙方當事人來看。在判決書中,法官需要通過當事人出具的證據來認定事實,同時決定支持還是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但是當事人出具的證據或者主張的事實是大量且復雜的,這些信息并不是都與案件爭議密切聯系,審判者必須經過分析和總結,將必要的信息挑選出來,將復雜的事實情節轉化成簡單的法律關系。這種化繁為簡,化事實問題為法律問題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對判決敘事的修辭。審判者在這種裁剪修辭中,可以通過控制裁剪的內容從而控制“受眾”的信息獲知,以影響受眾對案件的判斷,最終使受眾更加容易接受審判者對案件的解讀和裁判。但是法官在對案件事實分析和總結的裁剪修辭中必須以案件基本事實為準,不能故意將有利于一方的事實刪去。在一些案件中,審判者片面地壓制一方的有利證據的出示,只顧為自己的言論做說客,而絲毫不立足于案件的事實。這種企圖利用裁剪修辭達到其他目的的行為于法于理都說不通,必然會遭到當事人的強烈反對,自然不是有效的修辭方式,達不到使當事人服從和接受的目的。其次,案件的關注群體也是影響司法判決修辭的重要“受眾”因素。“受眾”可以依據年齡、智力、文化程度、職業和個人修養等等各個因素劃分,對不同的“受眾”應當選擇不同的修辭技巧。信息時代的案件的關注群體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關注群體,一個重大案件的關注群體甚至涉及各個層級的“受眾”,司法判決想要讓每一類“受眾”都接受認可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所以裁判者必須判斷不同“受眾”對案件的影響能力,關注“受眾”本身在社會中的話語權問題。意思很簡單,裁判者在不能說服所以“受眾”的情形下,挑選出那些關注案件且經常性表看法和意見的民眾,特別是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力的話語者,比如微博名人,著名評論家等等。所以在司法判決的行文過程中必須注重對判決“受眾”的分析,來獲得法律和社會共同的接受,達到司法判決喻情于理法,集制裁與教育一體的目標。
(二)根據語境的不同選擇不同的修辭方式
語境分析是修辭的重中之重,說服的.有效性也主要體現為語境的價值關注。所謂說服就是在“話語者”與“受眾”之間產生共鳴,并且這種共識可以在“受眾”差異化的情形下依然存在。這種體現語境的修辭情景對司法實踐來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法律修辭領域,修辭情境可以體現出一定的語境,這種修辭情境可以表現為案件之中各種事實的變化情況,同樣也可以表現為涉及聽眾的行為與決定的影響修辭者將特定觀點展現于聽眾的那些特殊因素。由此可見,這種情境關注不代表無休止的對現實進行遷就,而是拋棄了既定的客觀事實,進而將大部分的表達傾向于用語言描述可以解決的部分。就像是漢克斯曼和范愛莫倫提出的理論所描述的那樣:“修辭論證是一種言辭的、社會的、理性的活動,其目的是通過一系列的陳述來證成某一立場并使理性批判者相信這一立場的可接受性”。所以,要使用修辭來說服一方的時候,修辭雖然并不像直入主題的分析那樣具有強烈的目的性,但是在具體的論辯場合,要說服聽眾最有效的手段還是通過使用修辭情境來加強自己的語境。好比在判決最終形成的時候,傳統邏輯和經典邏輯僅僅通過分析推理與論證的結構形式,相比之下新修辭學主張的非形式邏輯更加傾向于實質要求中推理的語境等相關方面。在修辭學中,成功說服聽眾的標示就是使其都達到一個共識,是所有演說者的最終目的,當然修辭學的目的也是如此。盡管根據特點不同的依據會產生不同的分類,但當這些應用適用于司法過程中時,都必須在具體的情境中體現出證據、事實、標的等,所有主體達成的共識必須有一定的關聯,可以是互相的理解、對知識的共享、或者雙方完全達成一致。由此可見,在判決中若是希望清楚明了的對法律進行講解,通過特定的情境來表達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分析受眾的情況而達成共識,再使用各種修辭論辯的方式,并且合理的衡量價值因素在司法中的體現。在哈貝馬斯等學者的眼中,法律本身就與修辭學密不可分。法律是一種以說服為目的論辯手段,法律解釋和推理等眾多法律方法存在著一定的價值缺位,而法律修辭的方法正好可以彌補這一價值缺位的部分。這種認可法律修辭方法價值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肯定修辭對說服“受眾”的重要作用,修辭說服本身就是一種體現法治精神和人文關懷的語用活動。
四、結語
伴隨我國建設法治國家進程的推進,公民法律意識逐漸增強。反映在司法活動上就是,訴訟當事人不僅僅要求司法判決嚴格依法裁判,同時也對司法判決說理提出了很高要求,這也導致了司法實踐中應當更加注重增強司法判決的可接受性。從修辭學角度來說,還有很多對司法判決可接受產生影響的修辭手法。司法實踐中必須加強對修辭學以及語用學的研究,從更深一層次把握增加司法判決可接受性的方式和手段,提高處理質量和效率。同時以判決的可接受性為基礎,強化法律對民眾的教化和引導作用。
【司法判決可接受性論文】相關文章:
判決小學作文07-22
等待判決散文11-10
司法責任制論文05-24
司法鑒定工作論文精選04-27
行政壟斷的司法救濟論文03-09
最后的判決童話作文09-08
離婚判決書11-30
判決書格式11-29
行政判決書08-30